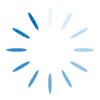沈娴一惊,瞬间又镇定下来,“姐姐身子不太好,我平日里也会帮她理家看账。”
年舒笑得疏离,“如今家中事多,你多操劳些,我也放心。”
沈娴道:“这是自然。”
年舒想起一事,“对了,母亲院子里服侍的这些人不得力,从今日起全换了吧。”
沈娴面有急切:“一时之间,恐不能找到合适人手。”
年舒道:“无妨,我会着人挑些过来服侍,回京前,再重买些合适人调教就好。”
沈娴见他神色玩味,亦不敢多言,只能答应。
不一会儿,明月带着神针堂的大夫重新来为柳氏开方,年舒见并无大事才放心离开。
见过母亲,自然要去看看他那位中风在床,一病不起的父亲。
提起沈虞,年舒心情十分复杂。他生他养他,他能有今日,父亲的养育栽培功不可没。这一面,他是感激的,也是他不肯背弃沈家的缘由。
可他这位父亲生性专制独断,又多猜疑,先是宠幸妾室坏了家中嫡庶规矩,后又嫉妒兄长才能,虽予家主之位但以父权威压,使他多年来有志不得展,郁积难舒。更遑论他以家族荣耀为由,放任白氏逼死年如,暗害君澜,桩桩件件已让他们父子早已离心,更谈不上所谓亲情孺慕之思。
白氏的松风小筑就在眼前,年舒突然不知该与沈虞说些什么。
缓步踏进院中,与他记忆中的模样一模一样。
亭台楼阁艳丽非凡,与从前别无二致。
什么节俭省流,不过说给他人听罢了。不论何时他的父亲从不会亏待自己,虚伪自私的话这些年年舒早已听够。
院中人见到他纷纷行礼,他径直往屋中走去,迎面已有丫鬟迎上来,“见过四少爷。”
“老爷在何处?”
“在夫人房中。”
年舒冷笑出声,白氏竟敢许下人称她“夫人”,那丫鬟自知失言,立时下跪请罪,“是奴婢一时口误,还请四少爷责罚。”
明月见年舒眉宇间全是厌恶,不由喝道:“还不带路,稍后去管事嬷嬷处领板子。”
丫鬟不敢争辩,揩着泪起身,“是。”
白氏房中一贯精致富贵,且不说幔帐寝被非苏绣蜀锦不用,便是金器玉雕亦是铺陈各处。此刻仙鹤振翅的青铜香炉里燃着大把苏合香,房中满是甜腻糜烂的浓烈气味,让人一嗅到便头昏脑涨。
年舒轻遮口鼻,往挂了百蝶穿花蝉翼纱帐的黑漆雕花大床走去,撩开纱幔,只见沈虞仰躺在锦被中,面容凹陷干瘪,两颊异常潮红,嘴唇干裂大张,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,大口大口吸着气,喉间不断发出哼哧声。
“还不快灭了炉中的熏香,再将窗户打开!”
那丫鬟在年舒威喝声中慌了神,连忙去开窗,明月也急奔出去将跟来的大夫请了来。
年舒见他眼珠浑浊,神思全然不在,连忙拍打他的脸唤道:“父亲!”
沈虞似是分辨出他的声音,喉间声音越发大了起来,无奈身动弹不得,只能使劲握住年舒的手,拼命挣扎。
好在明月领进来的大夫急忙从诊箱抽出银针,在他天泉、太冲、涌泉几处大穴上施针,他方才渐渐呼吸平顺下来。
年舒道:“如何?”
那大夫摇头,“亏损过甚,气息衰败,老爷这副身子已成枯竭之相,实在无力回天。”
年舒小声道:“还有多少时日?”
大夫道:“不过三五日光景。”
年舒沉吟半晌,对大夫道:“还请您继续开药治疗,能拖一日算一日,沈某自然感激不尽。”
大夫笑道:“沈大人客气,且不说医者不能弃病人不顾,便是看在宋小少爷的面上,我亦当尽力。”
这人出自神针堂,定然知晓君澜与吴迁的渊源,年舒言谢道:“这几日还要劳烦您住在府中,每日用药你写了方子来给我瞧,再行商议下一步诊疗。”
大夫心领神会,点头自去开方抓药。
沈虞已听见大夫的诊言,知道自己大限将至,顿时心灰意冷,脸色更加灰败。想他一生风光,不曾想到头来落得身残体败,瘫死床纬的下场。
他落得如此境地究竟是谁所害,一切皆是白凤倾那贱人所为。
他赎她出风月场,给她名分荣华,情爱尊重,为了她,不惜与妻子儿子生了嫌隙。可她是怎么对他的,串通沈秦那个老贼,为沈年尧那个畜生谋夺家主之位,害死了年曦。
眼下焉知已在危险之中。
不,此时他还不能死,沈家绝不能落在这起人手中,否则他如何能去地下见祖宗先人。
想到此,他握紧年舒的手,艰难开口,但还是发不出正常的音色。
年舒示意他莫急,只问道:“兄长的死是否与白氏有关,若是,您就点头。”
沈虞急急点头,又摊开年舒手心,一笔一画写到“秦”字。
年舒问道:“沈秦?”
沈虞再点头。
至此年舒已在心中将事情拼凑出了七七八八,只差年曦为何会亲下矿洞的理由,还有便是邹氏的死是谁下的手。
他心中虽有猜测,但没有证据。况且案发已有二十余日,恐怕罪证早已消灭,要翻案治罪怕是极难。
眼下他也只能安慰沈虞:“父亲先好好将养,余事儿子自会处置。”
沈虞轻轻闭眼,方了一桩心事。
年舒见他身不能动,口不能言,留在此处定有危险。眼下他还不能死,有些细节还需向他求证。于是,他命人将他挪出松风小筑,住到自己院中。
果然,此事一出,白氏已匆匆赶来,委屈道:“舒哥儿可是嫌我照顾老爷不周。若有不妥之处,你直言便是,何必这样折腾老爷,他又在病中,万一有个差池可怎么了得!”
她一贯的伎俩是推脱自己的责任,再倒打别人一耙,年舒司空见惯,不以为意,“白夫人多虑了,我离家多年,甚少照顾父母,如今父亲病重难愈,我不过是想尽孝父亲身前,白夫人不会连此机会也不给我吧。”
白氏听闻此话,立即赌咒发誓:“若我有此心,必叫我天诛地灭。我原也是担心老爷,姐姐也病着,几处事情凑在一处,也是怕你累着,怎就叫你误会我生了别的心思。”
年舒道:“夫人有心也好,无意也罢,并无所谓。眼下家中事多,你只需安分守己,看好年尧兄长,切莫生了旁的心思。”
他如冷箭般的目光射向白氏,她不由一阵胆寒。
回家不过几个时辰,年舒已料理清楚许多事情,其后他又请来年浩问道:“怎么不见秦叔?”
年浩道:“年曦兄长去后几日,秦叔整理砚场账目,见通州有笔账目不清,说是怕误了后期石材进购,半月前就去了那处查看。”
年舒道:“走得这么急?”
年浩道:“我也疑惑,与他商议不如等年曦兄长此间事毕再去不迟,他却说是禀明了大伯父,大伯父要他即刻上路。”
年舒不再多问,又唤来宋理,“你即刻派些可信的人前往通州寻找沈秦,务必探到他的下落。”
说着他又与宋理附耳嘱托几句,方才叫人散了。
第97章 密谋
晚间,白氏在前边灵堂随便应付了些时辰,借年尧身子不舒服为由,带着他回了松风小筑。
“母亲,父亲眼下被他带走,可怎么办才好?”
“慌什么,他不过是瘫在床上的废人,口不能言,身不能动,不足为惧。”
“就怕神针堂的大夫把他给治好,到时咱们功亏一篑。”
“他的身子早被酒色掏空,加之那毒,怎会一两日就能治好”,白氏想到此恨道:“只差一步,沈家就是我们的了,没想到解决了福贵,这个老不死的还派了别人给沈年舒报信。”
“母亲,眼下我们该如何?他回来,我们已不便行事,若再查出点什么,岂不是。。”
白氏道:“又不是你我动的手,真出了事也算不到我们母子头上。不过你先稳住沈娴那贱人,她莫要坏了我们的事。”
年尧道:“她满脑子做着当家夫人的美梦,自是清楚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,才能得享荣华富贵。”
白氏忧心道:“她始终不太妥当,待事情了结,便悄悄处置了吧。沈年舒不会在这里待上一辈子,早晚会回天京去,到时候沈琪那小子又能翻出什么浪来。”
年尧道:“母亲思虑周全。何况秦叔还去了。。”
白氏摆手:“不到万不得已,我不会行此险招,毕竟沈家倒了我们也捞不到好处。”
年尧道:“我管它倒不倒,要不是柳氏和她儿子,我与母亲何至于此。沈虞那匹夫嘴上说着疼爱我们母子,可沈氏还不是给了大房,要我们看他们脸色苟活。我如何甘心?!”
说到激动之余,牵扯旧伤发作,他立时抽搐起来,白氏连忙上前抚着他的胸口,急道:“何必动气,气喘发作起来,又折腾自己的身子。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