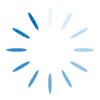“有此证据,可请刺史大人彻查此案,到时候定能找出凶手。”
见他欢喜,年舒不由也笑了,“明早我去见刺史岑彧,用不了多久定会还沈家清净。”
君澜看着熟睡的焉知,“这孩子亦可安心了。”
年舒不解他的话,君澜又将刚才焉知的惧怕与担忧告诉了他,年舒叹道:“这段时日真是难为他了。”
似是想到了什么,他眼中盛起愧疚,“当初你比他还要艰难许多,君澜,沈家终是亏欠了你。”
君澜摇头道:“我说过,有你,可抵我心中不平不忿。”
年舒心疼地抱着他,恨不能将之骨血揉碎,再融进自己体中,“若有一日你后悔,尽管将我的命拿去。”
“我要你的命做什么,”君澜闷在他怀中轻声道,“我只想你永永远远地陪着我。”
年舒很想答应他,但不知为何想开口却迟疑了。命运无常,他已然深刻体会,如今再也无法轻易对他承诺,“君澜,若我一时因别的事不能看顾焉知和沈家,望你能不计前嫌,给予他一时照拂,帮他度过难关。”
心中袭来不安,君澜猛地抬头看他,恶狠狠道:“你又要瞒着我做什么?”
他像只被踩脚的小兽,龇牙咧嘴的模样甚是可爱,年舒不禁捏着他的耳朵,笑道:“不敢,此生只听宋君一人吩咐。你让我去哪儿,我便去哪儿,绝不走偏半步。”
君澜贴着他的胸口,闭上眼睛,满意地笑了,“我困了,你背我回去吧。”
年舒立时放开他蹲下道:“遵命!”
君澜跃上他的背,环住他的脖子,贴脸叹道:“要是永远不长大,永远和你住在这院子里该有多好。”
年舒回头挨着他的鼻尖,轻声道:“这可是说了傻话!”
不知为何,君澜鼻酸得厉害,只道:“你别离开我。”
年舒未语,背着他一步一步走在廊下,踏在白练的月光中,他恨不得能走地再慢一点,弥补这些年他与他之间的错过与分离。
在他温暖坚实的背脊中,君澜做了一个很长很美的梦,玉兰花树下,无尽芳菲簌簌而落,他与他坐在林间小亭,层峦翠叠,飞瀑银河,在这无人打扰之境,他们并肩携手笑看云卷云舒,白首一生。
--------------------
过年之前尽量做到日更~~希望大家继续支持
第99章 端倪
次日清晨,云州刺史岑彧亲自带人入了沈府,彻查沈年曦夫妇遇害之事。
年舒骤然发难,沈园一众相干人等皆慌了神,尤其是沈娴。沈府下人谁不知,她平日与主母走得极近,差役们要问的第一个也是她。
此刻她亦不敢再与沈年尧见面商量,只得强迫自己镇定下来,照旧张罗料理府中事务。
松风小筑得了消息,白氏虽有忧虑,倒也不是十分惧怕,“沈年舒的动作果然快,昨日发落内宅不过是表面做做样子,夜里请人验尸才是正经。”
沈年尧不紧不慢喝了碗中的粥,阴沉着脸道:“即便查出来什么,动手的也不是我们,一概推到沈秦和沈娴身上便是。”
提起沈秦,白氏脸上泛上些许不忍,年尧见状讥讽道:“母亲不会到此时还相信男人吧?”
白氏想起往过的亲密,轻声道:“他对我亦有几分真心,否则不会做到如此地步!”
“真心?”年尧嗤笑出声,“老头子当年可曾与母亲海誓山盟?到头来,还不是说弃就弃,他有了更年轻貌美的女人,早把您抛诸脑后!说到底,金银钱财在手胜过什么真心誓言数百倍!”
白氏面色几变,终是沉下心,说服自己道:“也是,是母亲犯傻了。算起来,我与他约定的日子也快到了,不知事情可顺利?”
年尧拾起锦帕,擦去唇边汤渍,狠厉道:“只要我们过得安逸富足,管他谁死谁活!”
待白氏还要说上两句,已有丫鬟来报,刺史大人请众人去燕山烟雨堂问话。
堂内乌压压地站满了人,管事及仆妇丫鬟各自分列,园中各房主子位于前列。因着沈年浩这些年帮着经营砚场,是以二房三房的人也被请了来问话。
说起来沈园虽大,但下人们伺候的主子却不多。
除了沈虞夫妻,白氏年尧及年曦一家算是正经主子,其余姨娘侍妾不过是谁得沈虞宠爱多一些,谁得人侍奉便多一些。
白氏同年尧到时,年舒正命沈娴对着人口簿子向岑彧说明园中人口来历。
“全部下人皆在此处?”
“禀岑大人,是。”
“各房人口也齐全?”
“除去老爷夫人卧病在床,其余人等皆在,”她看了一眼刚到的白氏母子,“不过,上月府中一位姨娘失了踪,虽报了官,但如今也未找到下落。”
年舒知晓她所说之人是莲溪,点头道:“我知晓了。”
岑彧虽与他官阶相差不大,但言语中却更恭敬:“既如此,本官命人逐一查问,若有情况再与沈大人相商。”
年舒道:“前排之人请岑大人多费心。”
岑彧拱手道:“大人放心,这是自然。至于老爷老夫人,亦会有人问询。”
年舒颔首,“静候大人消息。”
衙役们领命后,各自带着下人们前往整理出来的厢房逐一问话,白氏见状不由哭诉道:“舒儿做这般大阵仗是为何,莫不是家中又出了什么大事,还惊动了刺史大人!”
年舒道:“白夫人莫急,不过是兄长的遗体上查出些端倪,衙门差人例行询问罢了。”
白氏瞪眼道:“曦哥儿已入棺安息多日,身为亲弟,怎可再复验他的尸体,岂非让他魂魄不宁?”
“让兄长魂魄不宁的并非是我,而是夺他性命的凶手。何况复验兄嫂遗体,我已征得父亲同意,”年舒牢牢盯着她的双眼,些许玩味道,“白夫人质问我,可是担心我查出什么?”
攥紧手中的绣帕,白氏强自镇定,面上露出凄容道:“多年来,你我两房虽有争执,但总是一家人,如何能有真正仇怨。何况我也是看着曦哥儿长大,如今他身死,又怎忍心他的遗体被人反复作弄,怕不是有人要借验尸之名,报昔日之怨。”
她话音刚落,众人看年舒的眼色已有猜测,尤其是沈瓒沈琰兄弟俩面上顿时不济,后者更是出言道:“舒哥儿你虽身份尊贵,但到底是沈家子孙,何苦一回来就闹得人仰马翻?发现曦哥儿尸身那日,本已请了衙门验尸调查,都无异常,怎么偏生这会儿又生出什么别的痕迹事故,且不说把这园子里的人都疑上了,连我们这等门儿都够不上亲戚也牵扯了!”
年舒知晓白氏巧言善辩,但今日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口舌为箭,挑弄是非。如果不是为了焉知与沈氏名誉,以他今日之势,拿下白氏母子根本无需这般费事,这会子偏给出她申辩反驳的由头,攀诬自己的名声。
他怒极反笑,“三叔觉得短短一月之内兄嫂暴亡,父亲母亲病重,一切皆是巧合?难道您与二叔不曾怀疑背后或有阴谋,还是也等着沈家溃散,焉知无力掌家,好从中分得一杯羹!”
沈琰闻言大怒,拂袖啐道:“年舒小儿,别以为你如今是上官,我与你二叔就不敢多言,我们好歹是你的长辈,怎许你指着鼻子揣测污蔑!”
沈瓒亦道:“舒哥儿莫恼,我等并非袖手旁观,坐收渔利之辈。出事以来,我们两房也是出人出力,忙前忙后,不想却引来这般猜度!凭心而论,我同你三叔的确不想事情闹大,这些年沈家出了多少事,家声不如从前,砚墨行生意也不如从前,好容易近来有些起色,何苦又掀风雨,成为别家的笑柄谈资!”
年舒见堂中人神色各异,或惊恐,或气愤,或害怕,或委屈,但无一人真正在意年曦死亡的真相,他们各自心中打着算盘,想从这场变故中获取最大的利益,他觉得可笑至极,“二叔三叔还不知吧,我府中侍卫在云州城外密林中发现了福贵的尸体,我已命人将其送到了刺史衙门。”
“福贵死了?”沈琰惊道。
众人脸色再次大变,年舒道:“各位可还认为是我故意搅乱沈家?”
沈瓒指着白氏道:“白夫人不是说他去为老爷办事了吗?为何又死在云州城外?”
白氏急道:“二叔急赤白脸问我作甚,老爷的确是这么对我说的,我怎知内里情况?”
沈琰似笑非笑道:“兄长病后是您在照顾,我们自然只能问您。”
白氏立时呼天抢地道:“冤枉啊,三叔怎凭别人三言两语就疑到我头上,我在这个家中熬了这许多年,顶着狐媚的名声被看轻受辱,连带自己的儿子遭了罪也不能伸冤,到头来却落得这等下场!何苦来,尽管将罪名推到我头上,我顶了罪责,杀了头,大家也就安生了!”
说罢,她跌坐在地上失声痛哭,沈年尧见状自轮椅上俯身去扶她,因着身体不便,摔了下去,下人们也不敢上前扶,他狼狈道:“舒弟非要这般羞辱我与母亲才甘心!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