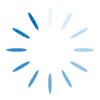莫松言的手在他腰际揉捏,双唇依旧紧贴着他。
萧常禹想要推开他起身:起床。
稍后再起,萧哥,春晨一刻值千金,你我别辜负了这美妙韶光。
莫松言一边吻他,一边用略微沙哑的声音呢喃。
旋即,萧常禹似有所觉,回想起梦中的那根树干,忽然明白自己为何会做那样的梦了。
他身子一软,任莫松言亲吻舔舐。
晨光投下绚烂的光斑,卧房内两人耳鬓厮磨,一直到下午方才停歇
莫松言烧好热水,抱着人去卧房清洗,脸上是餍足而充满歉意的笑容。
萧常禹圈着他的脖子,低头盯着莫松言锁骨上的齿印。
那好像是他咬的?
何时咬的?
他为何能做出这等事来?
莫松言垂眸看他,顺着他视线看过去,猜到他心中所想,笑得愈发满足。
这是萧哥为我刻的印章,是身份的象征。
萧常禹将头贴在他肩膀上,回避似得不再看那个痕迹。
胡说。
莫松言将人放到浴桶里,为他清理。
怎会胡说?不止这里有,背上还有呢,萧哥要不要看看?
说完不待他回答,莫松言便转过身展示后背的红痕。
后背两侧各有五道长长的印子,赤红不已,仿佛被利爪挠破一般。
萧常禹看得心惊:这是自己做的?
莫松言回过身,见他放大的双眼,立马躬身低头轻吻,而后道:这是萧哥你爱我的证据,不疼,反而是嘉奖。
萧常禹迟疑:怎会不疼?
莫松言轻压一下他胎记上的齿痕,痛吗?
萧常禹的脸立即一红,却道:不痛。
停顿片刻,他继续说:当时痛,但也不算痛,麻酥酥的。
莫松言为他穿好衣裳:我亦是这般感觉。
他又将萧常禹抱回卧房:萧哥,你多歇息一下,直接在床上吃饭吧,用过饭再盘账。
一晚加一上午,萧常禹确实觉得有些吃不消,因而点头同意了。
吃过午饭又歇息片刻后,莫松言将人抱进书房。
书房的太师椅上早已准备好软垫,莫松言将放在那里坐下。
萧常禹看着书房里一盆盆的炭火和水,还有桌子上的腊梅和糕点果脯,问道:你准备的?
莫松言一脸骄傲地点头:那是,专门等萧哥醒来盘账的。
辛苦了。
萧常禹微微一笑,心里又是一阵汪洋流过。
两人在书房内并排坐着,萧常禹拨弄算盘盘账,莫松言坐在他身旁看话本,喂对方糕点,虽然安静无话,却紧密相连。
将近傍晚之时,莫松言起身亲一口萧常禹的耳垂,然后去厨房准备晚饭。
腊月二十二日那天不仅是韬略茶馆歇业日,也是白梅开始休整的日子。
白梅人勤快,干活也麻利,没几日便将家里上上下下打扫地干干净净,当然,她没有打扫卧房。
厨房内干净得透亮,灶台焕然一新,所有的物品也被分门别类得放置在不同的位置,一切都井然有序。
不仅莫松言赞叹,连萧常禹都对白梅赞不绝口,他们像对待茶馆众人一般,给白梅一个红封,莫松言还特意又买了些年礼送给她。
白梅推脱几次,见他们当真要给,便道谢收下,转天就送来两大坛自酿的梨花酒。
自家酿的酒,一点心意,还请笑纳。
人家大老远推着推车特意送来,莫松言自然笑着收下。
他问白梅:浆洗作坊之事合计的如何了?
白梅道:差不多了,过了年便能开起来,届时还麻烦您帮我宣传一翻。
莫松言将两坛酒放进厨房:自然没问题。
今日的晚饭,他便打算做几道小菜尝一尝这梨花酒的滋味。
当然,他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而在微醺状态下的萧常禹。
微醺的萧哥别有一番滋味。
莫松言舔了舔嘴唇。
他简单炒了一个辣子鸡丁、香煎牛柳,而后将提前卤好的鸭翅、鸭肠等取出来一些,又炒了盘青菜。
他只吃肉,可萧常禹每顿饭必须有青菜才行。
将所有的菜摆在饭桌上之后,萧常禹也刚好将所有欠下的账目盘算完毕。
因为第二日无事,两人便放开了喝,推杯换盏之间,萧常禹脸上、脖子上薄红一片,醉眼迷离地看着莫松言。
老公,我的心为何跳得这般快?
他拉过莫松言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。
你能否感受到?
莫松言看着他通红的脸颊和认真的神情,忽然心生玩笑之意。
他摇头为难道:感受不到。
怎么会?
萧常禹诧异地睁大双眼,浓长的睫毛忽闪着:怎么会感受不到?
莫松言解释:手怎能听到声音?
噢,萧常禹放下他的手,有些失落。
过了片刻,他似乎想到什么,猛然站起身凑近莫松言,而后将对方的头贴紧自己的胸膛。
现在呢?
莫松言的耳朵正好对着萧常禹心脏的位置,强劲而有节律的跳跃鼓动着他的耳膜,鼻息间满是对方身上清冽的香甜。
他却道:再近些。
萧常禹听话地又走近一些,紧紧将人圈在自己胸膛里。
莫松言搂住他的腰,装模作样地听着,心里却在想喝醉的萧哥怎么如此可爱!
双手不知不觉开始肆意游动,萧常禹仿佛等急了,催促道:听到了吗?
莫松言仰起头,看着充满醉意的萧常禹道:听到了,萧哥,你想听听我的吗?
萧常禹点头。
莫松言猛地将人打横抱起:换个地方听得更清楚。
-
第二日是腊月二十四日,百姓祭祀灶神的日子。
莫松言摆放了一些祭祀的食物,而后和萧常禹一起敬香: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
祭完灶神,两人带着祭礼去往原主母亲的墓前。
每一次扫墓,莫松言的心境都会发生些变化。
从一开始紧张忐忑,到如今处之泰然,此时的他内心有一种自己已经在此地扎下根、非死不会离开的感觉。
这个感觉来得非常微妙,微妙到他自己也想不通他究竟是何时开始有这个想法的。
他牵着萧常禹的手站在墓前,行礼、上香、说祝辞,仿佛聊天一般将最近的事说给原主母亲听。
最后两人离开。
回到家之后,莫松言与萧常禹开始收拾打扫房屋。
基本不剩什么可收拾的了,白梅早已帮他们将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,只余下卧房需要他们自行打扫。
趁着天光正好,两人将卧房的被褥晾在院中,又相互配合着扫房、擦拭家具,而后又将冬衣拿出来折叠整齐,一直忙碌到傍晚下才停歇。
莫松言思前想后,在晚饭时将玉牌之事告诉了萧常禹。
我目前还是没有推断出这枚玉牌究竟是谁的,为何会出现在破庙的深坑里。
说完,他有些不安地看向萧常禹,担心对方会怪罪他隐瞒此事。
萧常禹闻言垂头沉思。
东阳县域广人多,姓莫的人家不在少数,但若是找出能雕得起玉牌的莫姓人家,倒真的只剩下莫忘尘这一家。
莫松言将玉牌拿出来给他看。
萧常禹观察着玉牌表面的花纹,果然与莫松言的玉牌如出一辙。
但莫松言的玉牌一直被他存放在木匣子中,而且这枚玉牌一看便有些年头,且有一种长期未见天光的土蚀征象,似乎在土中掩埋已久。
他明白莫松言为何现在才将此事告诉他。
你曾说过破庙中出现一伙人,似乎在挖东西
不错,王大哥也知晓此事。
可曾听闻过什么风声?
莫松言托腮道:这便是奇怪之处,我虽然不曾特意打探过此事,但世间万物总不会无声无息,这么长时间竟从未听过与此相关的传言。
萧常禹将玉牌放进帕子里包好:明日我们去破庙走一遭。
-
第二日,两人将萧常禹欠下的那些账目给王佑疆送去,之后携手前往破庙。
庙里的院墙仍旧是断壁残垣的状态,连莫松言捏碎的那块砖都还散落在原地。
庙中原来出现深坑的地方早已被人填埋,平整得看不出一丝痕迹。
若不是那枚玉牌作证,莫松言简直怀疑一切都是他的臆想。
萧常禹伸手指着前方:这里?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